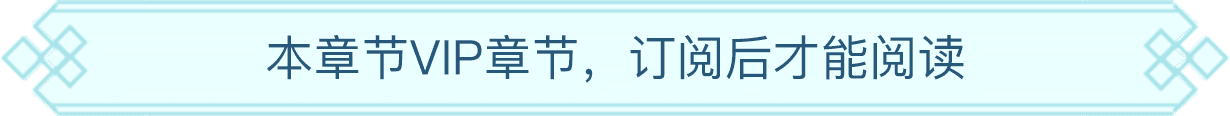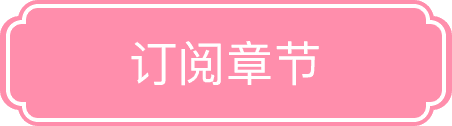白玉堂还未开口,便听白胡禀道:
“五爷。”
“说吧。”
白胡立在屏风后面继续说道:
“老奴查过了,府中仆人大多是签了长年卖身契的,只有一个名叫郭彰的花匠才来两月,三日前他的女儿前来看他。”
“嗯,把人带来。”
“五爷。”白胡有些迟疑的说道,“那郭彰两个时辰前已经离岛了,说是要到松江府寻个亲戚办点事。”
“哦?”白玉堂顿了一下,又道,“把他的女儿请到前堂去,只说爷有事相请。”
“是。”白胡应声退下。
“白兄。”展昭说道,“两个时辰足够到达松江府了,那郭彰若真有问题,此时怕是已经逃了。”
白玉堂整理着手上的白纱,抬头对展昭笑道:
“逃不掉的,既已经惹了五爷,他就应该有着这个认知。”
展昭本想说,此间一了,自己可以去把人追回,复又释然了,这人做事,还需要别人质疑什么呢?
“郭寒?”白玉堂看着手里的人皮面具,又看看堂下站着的已恢复清丽面容的女子,眉头微皱。
“是。”郭寒苦笑,在这人面前,自己竟是瞬间原形毕露。昔日那些有关温存的一丝一毫的幻想,该绝念了吧?
本以为这人既是阳光,天下红粉皆可照遍,那么自己,早晚也可分得点滴温热的。
却早该明白,身份所致,自己一直都在阴影里,或者说,这人的光从来就没有温度。
展昭身形忽动,下一瞬间,郭寒已被定住不得动弹,闪着寒光的匕首停在胸前一寸。
展昭淡淡道:
“若是冤屈,便该说明;若是罪过,也应该给苦主一个交代,何必轻贱了性命。”
白玉堂放下面具,脸上一片冰冷,“说吧!目的为何?”
目的?郭寒眼扫过桌上三宝,待看见一分为二的两只鸳鸯时,神情忽地有些狂乱起来。
不可能的!怎么会?
怎么可能存在一个人,可以与他携手并肩,一生相随?
抬头又见白玉堂始终冷若冰霜的神色,眼底的狂躁慢慢转为深深的绝望。
忽然就觉得累了---自己到底坚持了些什么?
转头看着身旁那不输与座上那人分毫的温润男子,轻声道:
“展大人,解了民女穴道吧,郭寒尽说便是。”
展昭抬手一拂,郭寒举着匕首的手缓缓放下,低着头静静说道:
“所有想杀包大人的人都知道,不先除掉展昭,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想要除掉展昭,却又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若是毒药,开封府里就有一位公孙神医;如果武功,放眼江湖,又有几人能敌得过南侠巨阙。而正好,锦毛鼠白玉堂便是这其中之一。”
白玉堂把玩着手里一只白色鸳鸯,面上不惊不怒,眼底越加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