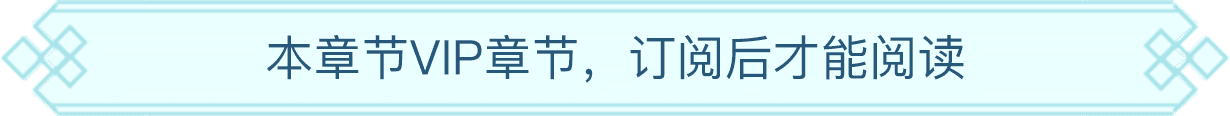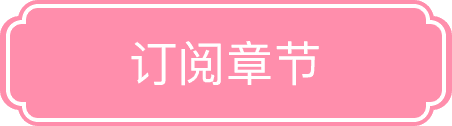“他能明白我的用心吗?”他轻声问着。
冯齐未答话,只是转头看向房门之外。
风势转大,烛火映衬之下的斑驳树影好似一头凶猛的野兽张牙舞爪,叫嚣着要将人吞入腹中。
回头,望着顾自出神的鞠缮,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少爷,他是真心悔改了,您就再信他一次吧。云弥这孩子着实让人怜惜,平日里便是只得了一点好的东西,面上看着淡然平静,心里却是惶恐的很,心怕那是不该属于他的东西,如今他好不容易过上了寻常的日子,少爷,难道您就狠心让他再回过沿街乞讨的生活吗?”
鞠缮闷声不语,只是一手曲指轻轻地敲着桌面,发出一连串杂乱无章的声音。
他心中又何尝不纠结呢,实则喝酒又如何,逛窑子又如何,世间这种男子多的是,多一个云弥不嫌多,少一个他自然也不会嫌少,而他,着实又何苦如此大动肝火。
“少爷,起风了,云弥他还跪在书房门口呢!”冯齐在一旁轻声提醒道。
他未答话,只是侧头看向屋子外头,看着摇曳的厉害的树枝,眼中划过了一抹犹豫。
许久,却是冷声说道:“让他跪着吧,我到要瞧瞧他到底能撑多久,说什么要跪到我改变心意为止,只怕是口上说说罢了。”
他冷笑了一声,起身走向内室。
“少爷,看样子怕是快要下雨了,他还只是个孩子,若淋坏了可怎么得了?”冯齐跟在他的身后。
“淋坏了自然有人会替他医治,又何需你**心。”
他一挥袖,硬生生的止了冯齐紧随着他的步子。
“可是少爷……”
“莫要再替他求情,”他打断冯齐的话,狠狠地说道,“这是他咎由自取,若再替他说上一句话,你就陪他去跪着吧。
此话一出,冯齐哪还敢多说一字,呆望着他的身形一转,被屏风隔去了身影。
回头,看到搁在桌上的饭菜未动分毫,他不由的多思起来。
还从未见少爷发怒到茶饭不进的地步,那怕是边关急报而来,他也未曾如今日之般食不下咽,这云弥难道还能比边关传来的消息更令少爷为难的吗?
他摇摇头,将桌上的碗碟悉数又收入了托盘之中,而后端出了房。
回身,看了眼桌上的一豆烛火,他伸手,细心地掩上了房门。
风吹过,卷起了他的袍摆,在夏夜时节,他却感觉到了丝丝地凉意。
微眯起了眼,他慢慢踱下了台阶,侧头看着一旁的厢房,轻轻地嗌出了一声轻叹。
唉,倔脾气遇上倔脾气,这不是两败俱伤又是什么,真是令人难以苟同啊。
收回视线,他循着石径小路,慢慢的步出了小院。
暗夜之中,云弥眯着眼,仍是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身形未动分毫。
一阵风吹起,细沙随之扑面而来,她一时不察,吸入了不少,顿时觉得喉头胸腔之中一阵的刺痛,忍不住轻咳了几声。
“呸,呸——”轻呸了几声,似乎那沙石亦随之离了她的身子。
抬头望望漆黑一片的天际,连星月都弃她而隐,不愿照映出她孤单的身影,平添心头一份孤寂。
有多久未曾这般抬头望天,低头看地,放眼四周只余她一人,这种感觉就像是曾经露宿街头日子一样。
果真是安逸的日子过久了,她就忘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了吗?
她只是寄人篱下,这里,不是她真正的家。
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家,亦没有家人,一直都是鞠缮对自己太好了,以至于她真将自己当回事,将这府里的所有人都当作了亲人。
是她太不该了,活该此刻跪在这里,独自品尝这份寂聊。
夜风更凉,落于脸上,竟多了一份湿意。
她有些木然的伸手抹了抹,发现掌心之间有些湿湿的,还未待她反应过来,黑沉的天空猛然间落下了雨帘来,顷刻间就将她从头到脚淋了个湿透。
这一下子,她可真是欲哭无泪了。
倘若将军此刻正坐在书房内,她到是可以趁着这雨势使使苦肉计,奈何看戏的人不在,她便是演得再逼真,也无人欣赏啊。
难道,连老天爷都要惩罚她不成。她只不过是喝了些酒,又不是犯了十恶不敕的大罪,怎弄得人神共愤的地步,她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这辈子才会落得如此多舛的命运。
房内的烛火暗了一些,似乎是被雨帘所隔,照映到她身前的树时,变得越发昏沉暗淡,投到地上的树影也模糊的难以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