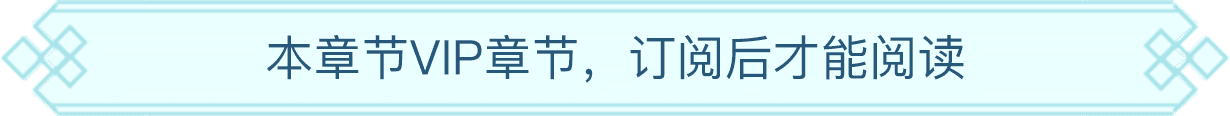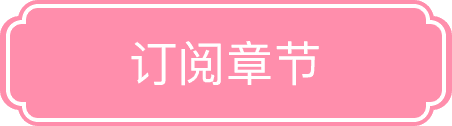秦义宣也只是嘴角一勾,俯身问道:“噢,怎样的自负法?难不成二次以身相许,今生既然许了你,既然再次以身相许,好吧,就等来生。”见过无赖没见过这么无赖,蓝西气得牙咬得卡兹卡兹响,她拉回理智再次善意恶声警告:“别怪我没提醒你。”
秦义宣这次不再勾着嘴角,反是大笑起来,笑声如朗月,不得不承认这只狐狸长得真挺妖虐的,尤其那双棕色的眼眸,带着深邃,似一汪澄净的湖水,让人一眼望不到边,若说司马昭然俊美如仙,这眼前狐狸便是妖虐如魔。
秦义宣抿着薄唇棕色眸子一直含着笑星,看着眼前那个小人儿,心里莫名的疏朗,对于她的警告视若无睹,薄唇微勾:“小西这是提醒什么,提醒我早日提亲?”
这人,这人,这个,简直没法沟通,无赖到太平洋。
这厮长得一副好皮囊,真是暴敛天物。蓝西眼神一潋,隐在衣袖中的右手早如待发的弓弦。
蓝西后面何时站了一华衣的似管家模样的人,他正将禀报,秦义宣眼神示意,管家俯身便下去了。
蓝西一个深呼吸自我调节,既随脸上挂上一抹春天般灿烂的笑脸,声音也柔媚异常:“提亲是吧?”长长的睫毛下一双眼睛闪着灵动的星光,里面的一抹算计光芒随着她眨眼瞬间一闪而过。“那要看你聘礼够不够咯,宝马必须得有,”右手抚额似在思考,“豪宅也不能少,聘金起码过亿,蜜月要出国,酒席要五星级大酒店。”自始至终说是温柔也不为过的眼神一直看着眼前的秦义宣,该死的狐狸,这么现代的术语眼神都不带眨表示疑惑一下。不过,这天看着似乎很好,没有清风也很爽,好像大嚎一首《农奴翻身把歌唱》,天时地利与人不和。
“哎哟,这天儿真好,适合婚礼。”蓝西低头不经意的整理袖口,很好,非常好,嘴角那抹狡黠的笑容。
眯着粽子眸子的秦义宣眼底一丝疑惑直达眼底,那些婚礼到底是什么,似乎挺不错。他心情大好抱胸看着蓝西一直呱呱不停吐着他不懂的名词。
多少年后当秦义宣真的因为蓝西一时刁难的求婚准备在这时代闻所未闻,他却备足了在她面前,只是早已注满的心,再也无法容许一丝的空间被放空,有些人,注定被伤害,有意却也不是故意,只道是无能为力。
这辈子欠的,下辈子再还。
那天秦义宣匆匆便走了,倒没再“为难”蓝西,蓝西顺利解手,便依循着路回到宴客大院,坐到司马昭然身后。
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蓝西对于眼前这位令人闻丧胆的大将军和翩翩谪仙的公子似乎也不再拘束,眼下,她压低声音小小问:“公子,这祁王。”后面的她把自己想像一股脑儿倒了出来,良久,司马昭然神色有些古怪略看了她,薄唇微吐:“或许,如你所说。”
这古怪在哪,蓝西当时到是想不通,等这满座宾客哗然一静,这宴宾的正主出场,带看清那位上座锦绣袍子,剑眉入鬓,郎目含星,如是神雕刻的五官,俊美带着一丝妖娆,那双棕色的眸子微转流彩连连,一身贵胄之气。
蓝西天灵盖地轰然倒塌,这当前的祁王老态龙钟的形象一下地基不牢,狠狠踏了,把她自认最骄傲的直觉打击得不复存在。
秦义宣,他就是祁王,那个吴国人人敬重的祁王,那个战场上与昭然将军拥有令人闻风丧胆的战魄,那个传说风流无限,流连烟花地,无情,残酷,冷血的祁王,却可以让人心甘情愿臣服于他的祁王,很多的很多关于祁王,蓝西也是这几天在街上晃荡时听说,这祁王,果然又一人物。
那当时他湖边受伤,一想到他当时狠绝的语气和那满目杀气眼神不禁冷上百度。后面军帐林子再遇,巧合?还是仅仅是时间问题?
还有自己一切的一切,这些真是巧合?
眼底飘过一层迷雾,思绪停留在那些磕磕绊绊的事情,上面各位大神外面敷衍里面刀枪厮杀的客套的话题她一个也没理,政治,本是如此,再好的国际关系,也是靠利益维持,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