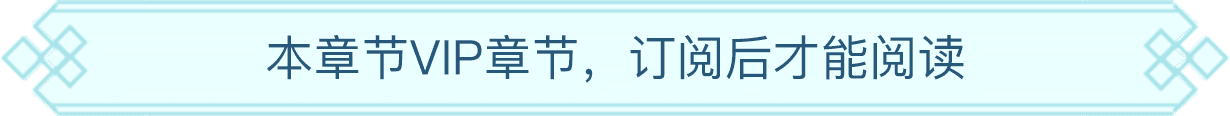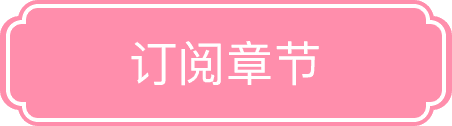市政市座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两下,秘书长才走到门口,一看市座不在,就随手接听了电话。
“喂,你好,是哪位?”听到对方直呼市座名字,又是女性的声音,料定是市座的女儿通话过来。“对不起啊,韦副市座不在办公室,外出办公了!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转告给我!我可以代为交待一下!”
韦恩琦听到自己的父亲并不在办公室,又不想说自己心中的事情,但又怕再没有下一次机会,她的父亲经常忙于工作,很少顾上家中之事,要是错过能解决韩文略杀人案件的机会,女儿就不太可能从校队脱身了。
于是她直接开口问,“我父亲回来的话,告诉他,务必给公安局的严贺进队长打个电话,因为我女儿学校出了事情可能会有所牵涉,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有关韩代表家的事情,秘书长你应该有所耳闻吧!可是他们却把事情压下来了!”
秘书长的神色变了两变,“你等着,我立刻去找韦副市座,请示他后立刻去公安局问情况!”他动了怒,韩家的事情居然会让公安局压下来,连副市座的家属都牵涉到其中来。这是怎么回事!不等韦副市座回来,他亲自给了韩西泽一个电话,当然这个人大代表的电话不是随便打的,但是市座的名义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非打不可!影响太大了。
但是这件事情捅到了公安局而且还压了下来,看来已经不容小觑,要避重就轻把事情搞清楚,不是很容易,他考虑了片刻,还是把电话打通了。
“喂,你好,这是市政办公室。对的,我们市座有事情找韩西泽代表!请通报一下!”
看来内线已经打通了,然后他又用手机给韦副市座报告这件事情。“副市座,对!我在您办公室,刚才应该是你女儿打过来电话!有件事情很严重,看来您似乎不知道,圣安中学有案子被公安局压下来了,对的,您的外孙女似乎是被牵涉进去了!如果不忙,请尽快去公安局了解一下!”
听到市座很快断掉电话,估计半会他也回不来,又接通内线电话,刺探韩家人的口风。
“是韩代表吗?”秘书长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压低了声音,缓和着口气。
韩西泽似乎没有买他的账,“你是哪一位?”
“是这样,韦副市座交代我给您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说是有要事要商量,可是临时有办公,所以我代打过来了。他跟我说,公安局的严贺进刑警队队长做私访到了他家,说是圣安中学出了点事情,想要了解一下内部情况,听说事情好像跟您家有关,可是又不便透露更多!现在,我只是代为市座,想来听听你的说法!”
韩西泽代表的眉头紧了起来,韩文略的事情他已经交待人把事情压下来消息应该封锁了,难道还有人在暗查吗?尽管他是知道这件事情在圣安中学私底下被人议论纷纷,但是还没有在社会上造成多大影响,即使没有被查办,也不该轮到市政来管!
“圣安中学的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就算是是跟我韩西泽家里人有关,有什么责任我们是要负的!韦任仪要是交代你向我听我的意见,最好让他当面来找我!你,就不要介入了吧!”
那边不由分说地切断了电话,秘书长再也沉不住气了,圣安中学出事情,一没有捅到社会上,二没有公开,消息封锁成这样,看来已经严重化了。不等韦副市座回来,他就先行一步到圣安中学去了。
微雨蒙蒙的气候,凉意习习。
裴咏怀终是从生死线再度挣扎过来,像女孩子那样漂亮的大眼已经了无神采。
林诗影看着他虚弱的神情,想哭,却知道自己不能哭。她摩挲着儿子的发际,“咏怀,你终于清醒了!”
“妈!”他微微地回应着,“爸爸、弟弟呢!”
她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怎么敢说裴青原是根本脱了手似的,不再来探视,而且也不允许咏仲再踏进医院半步,她的事情已经把这个家割成了四分五裂,让他看到这此情此景,那不是更不要活了!便忍着没说,只是极力抚慰着他,说了假话,“你爸,让咏仲去上学了!他要开车,医药费他在想办法!妈妈也不会放弃的,你乖,你一定会好的!”
“妈!”他用力地呼吸着,却是那么的艰难。
“咏怀!你听话啊,不再要胡思乱想了,要喝水吗?你看你!”她起了身去倒水。咏怀却挣扎着要起身。
“咏怀,你别乱动啊!你要起来吗?”她赶紧去扶他,可是儿子虚弱无力根本无法起身。她只得放弃扶他起身,只把他的床位摇得高些,便于倚靠。
“妈,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学校!”咏怀虚弱地问她。
“你不要急啊!等你身体好一些,我送你回去看看,这样好吗?”林诗影跟他商量着。
“我答应了教练要支持到元旦汇演的,可是现在我就住院了,好不甘心啊!”他想着已经没有办法支撑校队,不知道现在已经什么模样。想着自己会有一天与刘明诚地下相见,就无端地悲哀。
“妈,你不要骗我了!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不要离婚,别再怪爸和弟弟!”他侧过脸来看着母亲,眼泪停在眼眶里硬是没有掉下来。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如洪流倾泻而下,再无法克制自己,也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瞒得过儿子的眼睛了。
“咏怀!”她抚摸着他的脸,“你爸常常打你吗?啊?都是我对不起你们!一直没回来,让你们吃了那么多苦!”
她哽咽着,想把自己没说出来的话说出来,但又怕刺激他,但又不敢再欺瞒下去,他还会问,还是会知道。
“咏怀,是妈妈对不起你,为了救你,我才要离开你爸!别怪我!”她泪雨滂沱。
“他不能接受是不是?”咏怀伤感地回答着,“他不想认我了,是吗?是爸爸要离婚吗?”
“是我的错!裴咏怀!”她握紧儿子的手,“你听好了!就算你没有了父亲,我不会放弃你的!你听话,我会想办法救你!等你下了病床,你要做什么,我都随你!”
“咏仲知道你们会离婚吗?”他心似焚烧,想到咏仲无法接受父母离婚,自己会病故的现实,不知后面会是怎样结局。
“我已经顾不上了,他恨透了我们,怪你爸不管你,又怪我瞒他!而且这件事情,他没办法接受!你们不是亲生父亲兄弟的事,你就体谅一下他的心情吧!他也很痛苦的!我暂时不会跟你爸离婚的,你放心好了!就算有那么一天!”她继续摩挲着儿子脸庞,怜悯地痛惜,“我不会让你这么痛苦地离开!那样对你不公平!要是找不到办法筹钱救你,我一定想办法让他们接受你!啊!你要坚持下去,咏怀,听到了没有!”
毫无办法的,他应允地点点头。
“妈,你别哭!”他抬起手拭去母亲眼角的泪,清清楚楚地看到母亲头上的淤伤,“我不会勉强你,要是爸爸因为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打你,我不勉强你了!但是,你不要丢下弟弟一个人,不要丢下他!”
话到如此,还能说什么,她只有点头。
似乎把话都坦白说开了,压力就减少了。裴咏怀的精神慢慢好转起来,咏仲父子再没有来探视他,虽然带来不小的失落,总归已经全力抚平了他的情绪,渐渐地进入了正轨治疗,病情也稍有缓和。
秘书长从圣安中学回来的时候已经临到傍晚了。
韦副市座接到他的电话时没有再回办公室,直接就去了女婿家里。他倒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绊住了女儿,使得外孙女牵涉在内,不得脱身。
韦恩琦对父亲哭诉了女儿的遭遇,请求父亲把廉海平教练儿子的案件公正处理,以免汪晓瑾深陷校队,会受到不小的伤害。
韦副市座卸下了官腔,和女儿分析情况,“恩琦,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汪晓瑾她自己不会出尔反尔!她答应了你完成首演后不再与裴咏怀联系,那是有她自己的做人原则的。要是她违背了自己承诺,才会深陷悲剧之中。况且,这件事情有缓和的余地,你们不该作多干涉,即使是教练有意放手,她自己还会回到校队去的!”
“可是,爸!廉教练不是不通情理的人,他也是因为……才会留住汪晓瑾,她跟我说了,本来自己只是候补,就是因为刘明诚已经死了,还有……裴咏怀病重住院,她才全力顶上的。你想想,只是还他一个公正,他一定会放弃晓瑾的!这样晓瑾一个人在校队里很难撑的……”她苦苦劝着。
“顺其自然吧!”外祖父似乎是不能认同她的想法。
“可是……爸,我本意是想,你帮个忙,把刘明诚的案子处理了,教练就会放开汪晓瑾,到时候,我把她送到江老头子那里,她也随着出国,远离这个伤心地了!”她竭尽全力地表达着自己。
“恩琦,你的心情我非常明白!你要牵着女儿的手,不想让她跳悬崖……我就怕你们,干涉太多,反而事与愿违!”他缓缓地表述着,再抬眼看了看焦急的女儿,“至于这件事情,看来我不出面是不行了!但汪晓瑾自己的意思,你也得尊重一下吧!对了,圣安中学发生的人命事情,你知道多少?”
突然啪地一声,汪瑛忻将案卷掷到桌上。
“你这什么态度!汪瑛忻,你最近又做了什么!”看着女婿神情嚣张跋扈,他很是不满。
“爸,这就是韩文略的案宗,你不是要了解吗?我连带卷宗从严贺进那要到了,什么情况你自己可以仔仔细细地看!”他连带不屑,不以为然地看着自己的岳丈大人,以为他可以从里面得到什么提示。
不过仿佛他似乎有理,韩西泽是市委人大代表,韩文略是他的孙子,如果要硬办韩文略,就会得罪韩西泽,那么两个人就会形成政敌,往后在官场上两家就会成为死对头,对自己的岳丈是极为不利的。
当岳父的看了两看汪瑛忻,不明白他是怎么弄到公安局的刑事卷宗,又是怎么弄来的,但他可以由此了解其中缘由,也顾不上考虑手段问题了。
他打开卷宗来亲自过目,汪瑛忻如同讽刺一样反击他,“爸,你认为有必要办他吗?你考虑好了吗?是不是真的把案子重审,把韩 文略抓起来,就算完事!他廉海平就此松手,我汪瑛忻还没有这么窝囊过!是不是给他个说法,他就解散校队?在我看来,不会!他摆明了现在是在继续维权,可谁买他的账,韩家人是完全不可能,公安局是被施压了!你出面是有用,可是后果呢?”
韩副市座的表情变得凝重了,他轻合案卷后质问汪瑛忻,“你觉得韩西泽是个护短的人吗?”
“不用说了,爸,即使他不是护短的人,但一个儿子,一个媳妇,还有三个老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加上韩家两代单传,你心里认为他将会做什么的决定!”汪瑛忻拉起一丝暗晦的笑。
“好了!什么也不要说了,你是觉得廉海平是在利用汪晓瑾,逼我们家用官职权力来翻案,那么请问,他如何得知,汪晓瑾会有如此大的背景!”
“爸,想也不用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在长源市,谁不知道我汪瑛忻是靠老婆走上官场的,谁又不知道汪晓瑾的外公是长源市副市座,连她的外婆都是市教委一把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也不能避嫌!”他如是这样正言,又是理所当然的奉承着。
韦副市座的眼睛又投向了他,汪瑛忻什么时候学的圆滑之术,好像还言之凿凿般,正如同他所说,韩文略涉嫌故意杀人,理应公事公办,却招架不住家人的痛哭流涕地求情,才利用职权护犊!但汪瑛忻却反对韦恩琦的做法,力劝自己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插进一手,否则不但是政局面敌,更加是为他自己在后区议员选举之时,不便得罪自己这票,也更加不能得罪韩家那票!汪瑛忻是自己女婿,拉他一票是人情,不拉这一票也无伤情分,可是他这种态度实是把他给惹怒了!
想及如此,不由地恼怒,回敬给女儿怨气,“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解决!至于汪晓瑾怎么样,我是管不了!以后也别找我!出了事情,你们自己负责!真是气死我了!”
他拂袖而去,准备把韩文略的事情重提,侧面打击韩西泽放弃护犊,至于他会怎么样,自己也无法料得住,再过几年自己就要退休了。他也不想在这样的事情上自己处理不当晚节失保,否则传出去,也只有被贻笑大方,更让自己声名扫地。
韦任仪回到自己的家里,已至凌晨。年近花甲的他虽然身骨硬朗,思维神敏,但一想起韩文略的案子就忍不住要担心,韩西泽跟他以往是同学,后来又是同僚,也有几分交情。加上女儿现在要求他出面翻案,那么就会正面与韩西泽交锋,很有可能就伤及两家交情,一个处理不慎,就会殃及池鱼。
他是不明白韩文略是如何惹上了官司,也不了解其中缘由,但外孙女已经牵涉进去,也唯恐人心叵测,年轻不懂事涉世未深的汪晓瑾要真被人把住,逼得汪家不得不要自己出面解决这起案件,看来也是颇有把握,不由得他不得不去理会这案件,尽管案卷已经看过了,但如果韩家人不松口,继续将此事沉压不得昭雪,总有一天这个事情会流传出去,到时候,影响力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想及如此,不得不深深地叹了口气,摘下了老花镜,圆泽的额头又深深地嵌入了似刻的皱纹。
夜已入深暮,暗无日光,偶有雷声,隐隐而作,又似有打闪,光亮飞过,却只一瞬间,又了无影迹可觅。
冰冷的墓园深深寒凉,漫天飞舞残枝枯叶。远处的风声似是凄苦无声,又似同孤魂的泣咽般虚无飘渺!
踩着断叶的父亲站在墓碑前,痛怜地抚过儿子的孤苦的墓碑,抚过刻着儿子名字的刻痕,而五指颤栗。
这尚似无血无缘的父子,却都至情至义。
他低低地沉痛地呓语着,“是我对不起你,明诚,你说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似是叩问上苍,这世道无常,令人悲愁断肠,情不可抑。
他倘佯已久,才不舍离开,再望而三,路口一个苍老的模样,微薄之灯,映照孤单,亦或苍老。
似是看去,仿佛面目熟悉,却不想向前,直至年迈身影渐行渐近,才不得已而正视之。
而这个单薄老人正是长源人大代表韩西泽,他拄着拐杖,低三下四地求他放过唯一的孙子,“能谈一谈吗?”
廉海平愤懑交加,回敬有力,“有用吗?他能活过来吗?”
老人还想说什么,又无力说什么,究是自己孙儿罪责在身,而面前的人经历数次软磨硬泡,却将心磨成了硬铁,他也闻知两人虽非亲父子,却是至情至性,更相信他能体会失去亲人的痛楚,只得在刘明诚的墓前摊下年迈之膝。
“请你看在我这张老脸上,放过他!韩家就这么一命香火,不能断……”韩西泽低下花白苍苍的头颅,“我愿意为他,承担所有的罪过……”
廉海平的浊泪夺出眼眶,“十九岁的人,不值得您这样!”他转过脸去,“我也不要你们拿命抵命……我要他韩文略,亲自道歉……否则,没得商量!”落话掷地有声,转瞬折身而去。
他害怕自己会心软,动摇原则,让本是无所依靠的刘明诚彻底成为枉送的冤魂,自己更加愧对有加!
韩西泽似乎是看到了希望,浑浊的老眼里透出了一丝感激!
黯然暮夜的天空隐隐雷声,无法敞开,撕开的闪光,终是瞬间而过,撕不开黑,撕不开深邃,隐隐之雷,似是逼近,又似是缓缓地轰呜,父亲苦涩笑音,远远地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