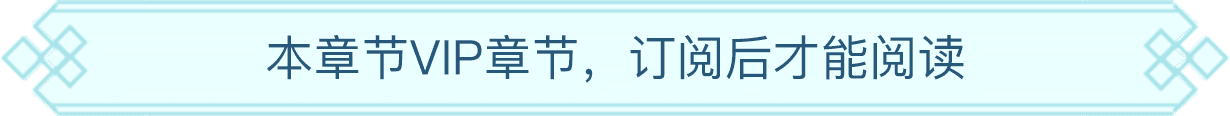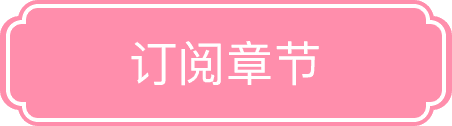他醒了,再一次被噩梦惊醒。
寒冷的夜风刮在他单薄的身躯上,带起一片疙瘩。
多少个日夜陷入如此荒凉的境界?梦里也难回故里,或许如冰封般的世界便是对他的惩罚。
他干咳了几声,嘲笑自己的自大。
没想到当初一阵风云的他竟是如此田地。
夜依旧深沉,如星辰如蹦跶着华尔兹,华丽而不加半分的实际。
“真像梦一般愚蠢呢。”他冷得直哆嗦。
曾几时,他游荡于灯红酒绿的酒会,黯然于白云绿草的草原,都不觉得有什么如梦如幻的。
非要这种绝境才是最美丽的吗?
他挪动了身体,像只可怜的臭虫,事实也本该如此。
他准备等死了,可是他却没有死,也不想死。
苟延残喘,像个没用的废物。
纠结于这个字干什么?死亡?怕‘死’,或者说是太多地接触‘死’了吗?
他苦恼地笑了,满是胡渣的脸看起来尤为荒诞。
他简直就像个乞丐。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时间如流水般流过,黑暗笼罩的天际涌出虹流,然后泛白,最终升起了淡红的圆球。
又是一个夜过去了,他勉强支撑起自己那精魄力尽的身体,颤抖地迈开脚步,却不小心踩住了一块碎石,然后就这么摔倒在了岩石上。
疼痛感好像被麻痹了,身体只感受到了一种震荡感,说不出是难受还是舒服。
他硬撑着往前面爬动,似乎死的时候也在前进并不是一件可怖的事情。
但是他注定失望了。
在又一次失误后,他支撑不住身体了,滑在了斜坡的正上方,直直地滚了下去。
丢脸,这么死去,太丢脸了。
他想道,随后陷入了一片黑暗。
“醒了吗?”
他再次醒来的时候,眼前是一个看起来刻薄的男人,他的胡子打岔,完全一副奸贼相,说的话也是冷漠极了。
“醒了。”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说道。
“看你这么虚弱,吃点肉汤吧。”男人冷冷地说道。
“不用了。”他闻到肉汤的油腥味,就感觉肠胃一阵翻腾,连带着身体也痛苦了起来。
“瞧我这记性,忘了这个样子是不能吃肉的。”男人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连道,“我马上去帮你煮一锅粥来。”
“谢谢。”他第一次真心的说出了这个词汇。
一直到男人离开,他还是久久无法释怀。
终究,还是没有死去,真是无聊啊。
他艰难地扭动了脖子,看向了床头的镜子。
里面照着的人真是不堪啊,头发乱,胡子糟,简直就是一副野人像啊。
可不幸的是,他知道,那个人就是他。
“认赌服输,我就是应该落寂地离场。”他轻叹。
门开了,男人走了回来,带着一锅粥。
“吃吧,看起来你受了不少的苦。”男人还是面无表情,甚至看起来就是凶神恶煞,但是在他看来,男人的面容其实是和蔼可亲的。
“谢谢。”他接过了勺子,只是咽下了几口粥水就已经无法再吃了。
“我吃饱了。”他对男人点头示意。
“如果饿的话,那么跟我说,我就在大厅里面,你一叫我就能知道。”男人还是冷着脸,端起了几乎还是满的罐子,走出了房间。
这个时候,他才感受到了极度的疲惫,连手指都无法弯曲,整个身体仿佛不属于自己了,这种感觉十分奇妙。
他开始注意起现在所处的屋子,这是个木制构造的房间,有着他身下整洁的大床,有着一个书桌,但是没有窗户,唯一的光线就是从木门的缝隙里渗透的灯光,而它的角落里堆满了柴火,看起来是个柴房,却有着标准房间的配置。
真想就这么睡下去啊。
他的视线变得模糊,眼睑缓缓地闭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再次被噩梦惊醒的他喘着粗气,入眼之处一片黑暗。
“我死了吗?”
他自暴自弃地想到,随后又自嘲地笑了。
要是死了,他也是该下地狱,怎么可能呆在这么安静的地方。
他揉了揉发胀的脑袋,迅速地回想起睡着前的一切。
“这么说,我还是没死成。”他没有感到高兴也同样没有觉得悲伤。
腹中忽地传来难忍的饥饿感,使他想起了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吃顿饭了。
现在的他,犹如一个最底层的流浪汉,而且还是连乞讨都不干的流浪汉,连混吃等死的资格也没有。
讽刺!
他的脑海没有任何停留地蹦出了这个字眼,想想也算正确。
确实是一段具有讽刺色彩的生活经历。
带着这份屈辱就此死去,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他掀开了被子,用脚在地面上左踏踏右踏踏。
很快,他的脚趾勾住了一双粗糙的鞋状物体,很快地套上了脚。
这是一双草鞋,看起来收留他的人家也并不是很富裕。
他迈着较小的步伐,在房间里摸索着,但是因为之前记忆下了整个房间的构造,他很快就找到了房门。
出不出去呢?算了还是找一找有没有吃食。
他很自然地扭开了门把,走了出去。
外面依然是漆黑一片,但是窗户透着月光,可以模糊地判断,这是间厨房,比较大的厨房。
这么说来,这是一间餐馆或者是旅馆之类的地方,不过看起来生意不太好。
他的鼻子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灵敏,但是还是发现了厨房的锅里有粥。
他拿开铁盖子,直接用汤勺舀了一勺粥,含在嘴里。
凉凉的,带着新鲜的谷香。
一直喝到饱腹,他才停止了下来。
真是,很久没有吃饱过了。
他甚至感到余味未尽,多么奇妙。
他打起精神,借着微弱的光线,看清了厨房的大门。
算了吧,还能干点什么呢?
他无趣地走回了柴房,关上了门。
又是一个早晨,厨房的光亮都渗透到了这个柴房里。
他感觉精神好了许多,起码没有那么疲惫了。
舒展了一下骨头,他走出了柴房。
“你还好吗?”男人正在煮饭,看起来乐在其中。
“谢谢你,我还好。”他回答。
“对了,你是哪里人啊?怎么会流落到这边?”男人问道。
“江西人,跟别人赌,然后输得什么都没有了。”他回答的时候很平淡,
“赌?”男人微皱起眉头,“年轻人,赌博伤身,是别人下套了吗?”
“不,对方说,不用赌,而我硬要给这场游戏加上个赌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更为冷淡。
“那真是不幸。”男人说道,“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帮我。”
“可以,反正我也无处可去了。”他回答。
从那天开始,他在这里工作了,这是一间在深山的旅馆,山的名字原本叫做水蛇山,但是由于不好听而在多年前被改为了水龙山。
他帮忙看店与基本服务,但由于客人不多,所以轻松了不少。
他始终没有见过男人的妻子与女儿,听他说,是因为他的妻子得了一种怪病,或许跟精神方面的问题一样,让她不敢见人。
日子平静了下来,如田园诗画一般的生活。
男人经常去后山种菜,一般的饭菜也都是他的劳动成果,味道也出奇的新鲜。
这是他所没有体验过的生活,一切都过于清心寡欲。
直到,他遇见了男人的妻子。
他从没有想到过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她’。
等到男人的妻子上楼以后,他才放下了一口气。
“对了,你的妻子犯病多久了?”他在那个时候问起男人。
“应该三年了吧。”男人自然不知道他想着什么,也就回答了他。
“果然。”他囔囔自语,“再那之后,‘她’就来到了这里。”
“你在说什么呢?”男人没有听清他的话,就问了一下。
“没什么。”他笑了笑,“只是想起了一个人。”
“什么人?”男人缓和了语气问道。
“男人。”他淡淡地回答。
“你不会有断袖之癖吧?”这些天让男人与他熟络了起来,原来只摆着个僵尸脸的男人也时不时会开个玩笑。
“呵呵,当然不是...”他其实心里想着的完全相反。
“你现在的生活还幸福吗?”他忽然看向男人。
“还行吧。”男人难得地露出了笑容,“经营着一家与世无争的旅馆,有着爱我的老婆与可爱的女儿,人生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呢?”
“与世无争。”他细细重复着这个词汇,越念越觉得奇异。
“你也喜欢这种与世无争的日子吗?”男人忽然问道,“小伙子,或许以后会有点无聊。”
“差不多吧。”他回答道,现在他穿着干净多了,虽然只是烂大街的普通衣服,但是衬托着他的清瘦,看起来还有一点悲世悯人的道人性情。
“年轻就是好啊...”男人感叹道,然后又严肃地说,“你还年轻,就想着窝在这个山哟哟一辈子?年轻人就该闯荡闯荡,等你老了,在这里住,养老的话,我都不会说什么,让你养老我还是养得起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过,其实我觉得我已经老了,心老了,也经历过了,或许许多老人也没有我的故事多,也没有这故事精彩。”
“是吗?”男人点了点头,“或许你是对的,但是既然你人还在,身体未老,还有什么可以称为老的呢?经历过了,再来一次新的不就行了吗?”
“可以吗?”他眼睛忽然亮堂了起来。
“你只要不把自己当成自己,那么怎样都可以成为新的开始”男人向往地说道。
这么久了,他看出来了男人是真的为了让他开始新的生活,这旅馆又没有赚多少钱,还要给他发工资,对于普通的旅馆老板来说,那就是疯了行为。
“是吗?但是可以先让我在这里休息几年,然后再谈志向吗?”他吐出了一口郁气。
“当然可以。”男人回答,看起来并不支持也不反对。
“那么,很感激你继续留我下来。”他淡淡地笑着。
“你叫做什么名字?”他趁男人出门之后,找上了男人的妻子。
“我叫做杜秋月。”男人的妻子说道。
“狗屁,我知道你不叫做杜秋月。”他有些无奈,“但或许现在的你都不知道这些。”
“你什么意思?”杜秋月惊恐地问道。
“我没什么意思,我不想插手这件事。”他干笑了一声,倚着的椅子也摇晃了起来。
“我如果不叫做杜秋月,那么我叫什么?”杜秋月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如恶鬼般尖啸。
“K,我来看看你们这些后辈的表现吧。”他不知何时已经走出了房间,并轻轻地关上了门。
“你从哪里买来的围棋?”他饶有兴致地问道。
“城里的供销社,不过除了那些文化人之外,大家连早点都自己做…”男人呵呵笑着。
事实上,这年份度假村游玩的人着实少,基本上也就是一些有余钱的老顾客,也都是看着人情来的,钱多不会来这种度假村,而大多数人也没钱去度假,所以这么一个毫无特色的度假旅馆,实在是没有什么收入。
“那,以后的日子就好受一点了吧,闲来无事,我们可以下下棋。”他执黑子,稳稳地落在了木制棋盘上。
“是啊,”男人的胡子还没有修剪,看着更吓人了,“我们基本没事做。”
“你的女儿去哪了?”他忽然问道,“我已经几天没有看到她了。”
“我送她去城市里上学了。”男人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学问不高,总不能误了孩子吧。”
“谁带着她呢?我看你女儿挺小的,”他提到,然后又叫道,“该你下子了。”
“你棋艺真臭。”男人走的是白子,“我也愁呢,孩子么,我们是让她住在别人家,但是谁知道她会不会不适应呢。”
“我确定她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他叹了一口气,“你觉得如果一个人最后都否定自己了,那么会怎么样?”
“那就不是自己。”男人说道,“年轻人,你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很危险的。”
“是啊,挺危险的。”他也感慨。
他把一桶从井里打出来的水灌入水缸,夏日的焰光下,热汗如蚂蚁般从他的背上爬了下来。
“只剩我们了。”男人失魂落魄地走了回来,“我婆娘去城里陪女儿上学去了。”
“是啊,她的尸体在哪里?”他冷冷地问道。
“谁的尸体?”男人的脑门上流出了冷汗。
“杜秋月,还有她的女儿。”他缓缓吐字,“还有她的老公。”
“你说什么?”男人暴怒,“她不是我的婆娘吗?”
“问题是,你是谁?”他问道。
“我是这里的老板...我是...”男人忽然吱声了,因为他回想不起自己的姓名。
“你是谁?”他的声音充满了磁性。
“你是谁?”男人的面容充满了恐惧,面部肌肉不断扭曲。
“你或许恢复记忆后能完全记得我,可惜你现在只是一个冒用别人思想的可怜虫。”他冷静地说道。
“你到底是谁?”男人嘶吼着。
“这就激动了?是你的谋略消耗殆尽了吗?”他不肖地看着男人。
“我要杀了你!”男人怒吼,转身就冲进厨房。
他冷笑着,一步一步地跟了进去。
男人在厨台上翻来找去,把本来插着刀具的模板扔在地上,口里碎碎念道:“刀呢?我的刀呢?”
“别找了,我全部丢到了林子里。”他倚靠在门槛上,显得悠哉,“这无趣的地方,你连计谋都没有施展。”
“你这混蛋!”男人喊道,“你有本事跟上来!跟上来啊!”
男人走乱了步伐,冲向柴房,眼神里充斥着疯狂。
“真是个白痴。”他淡淡道。
“你叫做什么名字?”他看着坐在对面的那个人。
“我叫做杜秋月。”那人的脸上涂满白色粉彩,勾起笑容,身边的洋娃娃上同样涂着难看的粉末。
“狗屁,我知道你不叫做杜秋月。”他看着这张脸就恶心,“但或许现在的你都不知道这些。”
“你什么意思?”那人掉了一片白粉彩,看来像个鬼魂。
“我没什么意思,我不想插手这件事。”他摇晃起椅子笑道。
“我如果不叫做杜秋月,那么我叫什么?”那人疯狂大叫,导致帽子掉了下来,露出了狰狞的面容。
那就是‘出门’的男人。
“K,我来看看你们这些后辈的表现吧。”他走了出去,轻飘飘地说道。
“这潜移默化的本事倒是褪色了啊。”他盯着柴房大床底下的地道,“仅仅骗几个普通人?”
“倒是可以猜出来,你先是在来的路上杀了那个女人,然后扮成她,用你的催眠类方法让别人以为你是她。”他大喊。
“然而,你自己就是一个入戏太深的人,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了她,后来杀死了她的老公与女儿,最后扮作两个人,骗过来往这里的每一个人。”他继续分析,“然而,在最近几年里,也就我来了之后,你感受到了我的存在,开始缓慢地排除外来记忆,可惜你自己的记忆已经没了,直到现在,你还是剩下一个外来记忆没有处理。”
“做个了结吧。”他囔囔,“我究竟该不该死亡呢?本来我早就想死了。”
他自言自语低走下了通道,黑暗在霎时吞没了他的身影。
“真是期待走出来的会是谁啊。”
他的声音从里面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