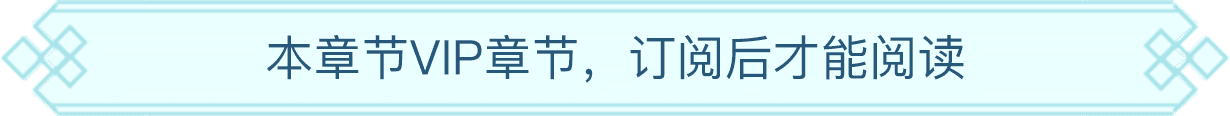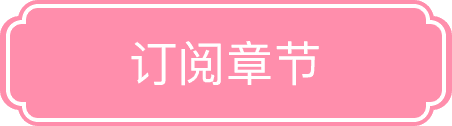田格子咬着窝窝头,坐在干草上发呆。
脑袋很痛,这大汉长得虎背熊腰,果然手劲很大。
算了,她逃不出去,也只能守株待兔,等着阎唯一来救了。心神一松,田格子很快就睡了过去,只是凌晨的时候,被冻醒了一次。
早饭很简单,一碗薄粥,两个窝窝头。看来大汉家里的经济状况,确实可怜得很。田格子奉上无限同情,更多的却是自怨自艾。
阎唯一整整一天都没有回音,大汉也焦躁不安:“你哥哥不在乎你吗?”
也许他恨她,但绝对不会不在乎她的!
田格子脱口而出:“不会的!”
说完了,她才想咬掉自己的舌头。现在应该顺着这大汉的话头,说阎唯一不在乎她,也许看看没有油水可捞,就放了自己也未可知。
真是一颗榆木脑袋啊……
田格子哀怨地仰躺在干草上,目光一动,落在成堆的木材上。这种木材的木纹,很紧致,看得出来是生长了相当长时间的。
如果她记得不错,有一种木头就是这种的生长方式,它叫红豆杉同,她的记忆里,也就只有一个地方,会生产这种树木。而她,恰恰曾经到过那个地方。
难道……她心里一动,仿佛有什么呼之欲出。
月光从天窗里洒下来,落在她的胳膊上,今夜的月亮竟然分外的明澈。可是她的心,却有点冷。
这大汉等着钱用,可是阎唯一却没有给出回应。她想错了,其实他并不在乎她。也许他们一别二十年,才会因为那点遗憾,让阎唯一多少有一点怀念吧?
苦涩地笑着,这一夜,是怎么也无法入睡了。
只觉得那月光像一把利刃的刃口,呼啦啦地把她的心剪成了两半,痛得几乎已经无法再用言语表达。
半梦半醒之间,耳边的蝉声,让田格子陡然清醒了过来。树木的清香,在大汉开了小半扇门的时候,格外清晰。
借着送饭的间隙,田格子看清了地形,果然隐隐有点熟悉,她和沈洁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栖身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如果她能够逃脱这扇门的话,就一定能够逃到山下。
只是,逃脱了……又怎么办呢?
田格子失神地接过了所谓的午餐,仿佛是定额,每一顿不管早中晚,都是一碗薄粥和两个窝窝头。
“你哥哥怎么还没有回音?”大汉不安地问,口气很不善。
田格子失神地看了他一眼,才低低地说:“我和哥哥,本来就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小时候,他一直很讨厌我的。”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蝉声结满树林的早晨,田格子忽然有了诉说的欲-望。和这个陌生人诉说着阎唯一小时候对自己的捉弄,原来那些记忆,竟然日久弥坚,竟然一点都没有忘怀。